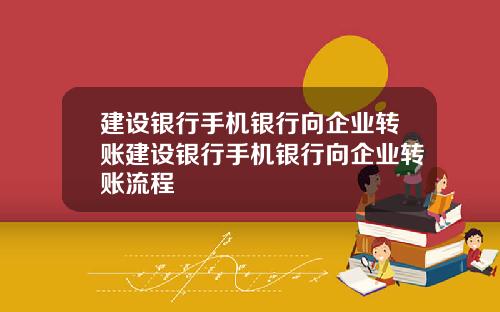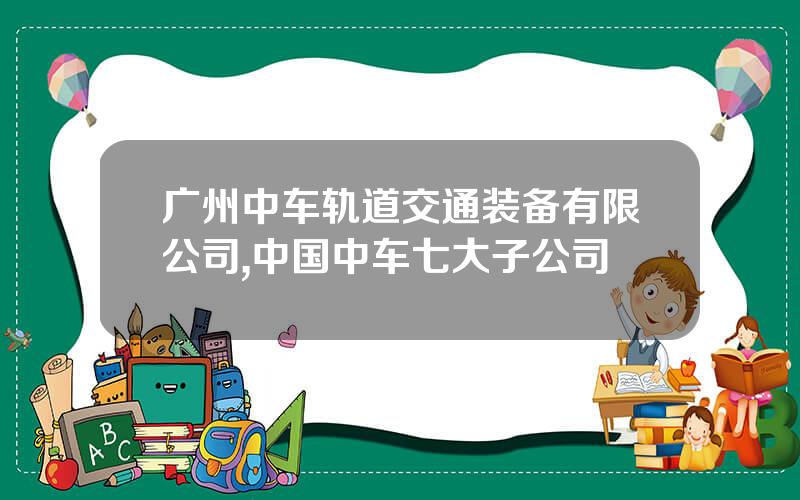【推荐】从平阴走出的气象大家刘衍淮洪堡基金会
作者:autumn 发布时间:2025-03-03 栏目: 金融理财 0浏览
列美·巴丁娜
右一为刘衍淮女儿刘美丽
商务印书馆2021年
第九届“十大好书”评选在京揭晓,《丝路风云——刘衍淮西北考察日记(1927—1930)》一书入选。
《日记》记事,始于1927年5月9日,迄于1930年4月19日,1077天无间断的西北考察日记,事无巨细地记录了为期三年的西北科考经历,是“中国西北科学考
查团”最为完整的考察实录,堪称中国气象学一代宗师刘衍淮学术起步阶段的成长史。
结缘气象·丝路风云
刘衍淮(1908—1982),字春舫,1908年7月18日出生于山东省济南市平阴县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。先后就读于平阴县城模范小学、济南私立育英中学。1925年,考取国立北京大学理预科。
1927年春,新文化运动以来民主与科学的影响早已深入人心,已是理预科二年级学生的刘衍淮,看到北大三院布告栏里一则“西北科学考查团”招聘气象生的告示,奋然报名。经过严格考试,他以19岁风华正茂的年龄,成为科考团最年轻的成员。此后三年,经行大漠、天山,饱尝辛劳,更收获满满。结束气象观测工作后刘衍淮前往德国留学,从而步入中国气象学、气象教育学的征途,终其一生与中国气象事业结下不解之缘。
1926年,德国汉莎航空希望开辟一条欧洲通往中国的航线,聘请了著名西域探险家、德国人斯文·赫定进行航线沿途气象考察。次年,一个在日后于世界范围内享有盛誉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成立,在北伐战争如火如荼之际,1927年5月9日,“西北科学考察团”从北京出发,踏上了漫漫征途。
恶劣的社会环境以及简陋匮乏的交通、通讯、后勤等物质条件,注定了整个丝路气象考察的过程无比艰辛,这在刘衍淮日记中随处可见:
“民国十八年六月廿一日,早两点一刻雨,至五十分。五点十分又雨,天阴云。十点半后,淫雨连绵,时下时停,至下午。……北山上的雪又顿增了不少。晚饭后,闲步河干,欲渡而登西山,河水宽,虽抛石河中以冀得踏石而过,然终以水深流急无效。乃至下游,跃过三数仄流,末一终未得过,乃归。本日等备明日作海子之游,数日来终未得一引路者。
廿二日,上午天晴。收拾毕,带二人、二马、五驴及什食、账房等,于十点三十五分东行,傍北山,石甚黑。十一点,过一房之北,不识有人居否。十分向东北东。十二点向北东,八分至特革斯,有居民五六家……询知路尚在南方,乃折西南。三十分方望见驴来,候十数分,又东入山。渐上渐高,路极崎岖之能事。五十分到一小达坂顶,下,仍单骑先进。路旁几尽系白剌,间有苔地生之松。一点后曲折东行,廿五分过一沟,上下小达坂,坂虽不高,然突立难行。……候多时,东登一坂,仍不见驴队之来。
两点后落雨几滴,至两点半后尚不见人来,乃归而寻焉。上下达坂,见驴印,乃迹而沿一沟南行寻之。此沟即生杨树之沟,此不过为其南部耳,名塔特里阿克阿鄂则。三点东行合大路,即克斯尔和屯来之路。北北东,由前候驴之达坂东西东行稍偏北,水流大,树林多,草亦茂,牛羊颇多,骤马疾行,惟以路多顽石,终难极快。渐见驴队,二十分渐北北东,地名乌朋尔阿鄂则。三点五十分,过喀拉达失。北行,四点至喀宜和屯。折东行,天浓云四布,大雨骤至,衣服尽湿,而身衣单衣,怎能不冷?暂息树下,而雨不止,不可耐,乃归寻衣,于牧者火畔易之,住此。鞍马、箱件,无一非湿。
支帐毕,移物其中,而雨犹不止,水渐入,而地又多牛羊之粪,秽污不堪。于帐中生火作饭,于是浓烟薰人,几不可耐。行路是有乐,亦有苦也!六时后雨稍小,六点半又大雨,至七点半后又稍小,以至于夜。住山沟中之拐弯处,多树株,高山夹流,水声涛涛,然草几等于零。即有之,今日马驴亦不得而食矣。自喀拉古尔至此约行有二十一公里,而绕至特革斯及折回绕远寻驴之所行,亦计于其中也。九点气压为588.5mm,温度10.5℃及6.5℃。点滴之雨不绝。”
1929年6月21日《日记》:“……北行,四点至喀宜和屯。折东行,天浓云四布,大雨骤至,衣服尽湿,而身衣单衣,怎能不冷?暂息树下,而雨不止,不可耐,乃归寻衣,于牧者火畔易之,住此。鞍马、箱件,无一非湿。”
在博格达山高山气象观测期间,刘衍淮独守空山。初春的天气变幻莫测,崇山峻岭中不时有风雪骤至,遮天蔽日,深山幽涧中,不时回响着野兽的长嗥。走在天池的冰面上,积雪下迸发出冰盖融裂的巨响,令人胆战心惊。刘衍淮毅然坚持,成为独当一面的气象工作者,以实际行动回应了外方团员对中方团员的偏见。
1928年6月初,建立库车气象站后刘衍淮独立承担气象观测,逐月将采集到的气象数据做成报表,定期寄送郝德和南京政府。1928年9月,考察团在距库车90公里的喀拉古尔山建立气象台,又从迪化(今乌鲁木齐)新招收一名气象生张广福,由刘衍淮进行指导,使库车地区气象监测工作在他离开之后得以延续。
流动大学·五四风貌
考察团的中外成员,有多位学有专长的专家。外方团长斯文·赫定,是享誉中外的著名探险家,他中亚探险积累的丰富知识,让刘衍淮受惠颇多。他利用赫定传授的知识,通过计算骆驼行走的步伐画出行程路线和距离,掌握了沙漠行程的测量技术。还在赫定的指导下绘制了几十幅考察速写,成为摄影、摄像的补充。
中方团长徐炳昶是留法哲学博士,刘衍淮随其调查民情、学习法文。袁复礼是美国学成归来的地质考古学家,刘衍淮与其一起寻找化石、学习地质学知识。黄文弼毕业于北大哲学系,在哲学、考古学研究及中国传统文化诸方面学识渊博,他携带的西域历史、地理等六箱书籍,让刘衍淮受益终生。
刘衍淮除了阅读原本就有基础的英文、德文版气象学专业书籍,还刻苦学习法、俄、蒙以及维吾尔文语言,还从迪化的俄国学者那里借来回鹘语著作《习畏兀儿及古突厥字》。在博克达山,刘衍淮一边例行记录风云变幻,一边学习《德文轨范》等著作,为日后学术道路的拓展奠定了良好基础。
考察临行前,考察团常务理事、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之一的刘半农,谆谆叮嘱气象生们“要把所见所闻都要详细记录下来,有些事当时看可能没什么用处,以后却可能有大用处”。
刘衍淮谨遵教诲,将三年、1077天的考察经历写成了近600页、35万字的《日记》,加上200余幅旧影、速写,忠实再现了考察团的西行之旅和民国西北风貌。
西北科考团数十人跋涉万里,辛劳累年,耗金巨万收集的气象材料,均由郝德负责汇集整理,然而大部分资料还未及公布就毁于二战战火。刘衍淮的《日记》所保留的第一手气象观测资料,则成为唯一可资参考的文献。
西北考察的三年,也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内忧外患之时。刘衍淮作为一名从五四运动发祥地——北京大学走出的青年学子,其政治敏锐性和爱国热情在《日记》中贯穿始终。他途中时常研读孙中山的《建国方略》,思考边疆“将来实业计划问题”。
济南是作者中学时代负笈求学之地,“济南惨案”发生,刘衍淮感同身受:“家乡糜烂,闻之痛然。”在库车得知日军占领济南,久久不能释怀:“拿来五月份《东方杂志》,内载五月初旬日人在济南演出之空前惨杀触目伤心,惨不忍闻。在昔繁华热闹之商埠,今已变为森严四布日兵根据地,巍然雄壮之城郭,已为颓废圮毁之日弹牺牲物,其戮杀之惨凄,甚于虎狼,其手段之鄙劣,有过鬼蜮。迟迟至今,已逾半载,仍系悬案,发指心痛,莫此为甚!”
1929年5月9日,刘衍淮在日历上奋笔标示“勿忘五月九日国耻纪念”,并写下洋洋千言日记,以铭记1915年袁世凯政府接受日本二十一条的国耻。1925年“五卅惨案纪念日”,又在日期后醒目标注“上海惨案纪念”。即使赴德留学身处异乡,刘衍淮的爱国情怀一以贯之,这也是他日后走科学救国之路的动力所在。
考察团中外成员的合作,充满了“命运共同体”下双方的真诚友谊与和谐共处。刘衍淮与他的学术引路人、也是引荐他到柏林大学攻读的气象指导郝德,更是结下深厚友谊。1969年,刘衍淮应洪堡基金会邀请访问德国时,又登门看望了这位良师益友。
科考团成员分属中国、瑞典、德国、丹麦四个国籍,由于思想观念、道德水准和信仰的差异,以及少数外方成员存有的对中国的偏见,在生活、工作中产生误会甚至矛盾冲突在所难免,刘衍淮总是本着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加以处置。他发现有外方成员拍摄“声调鄙俗,令人肉麻”的地方戏曲、过度惩罚偷盗团队骆驼的中国苦力,以及绘制违反条约的五万分之一地图等行为,总是第一时间告知中方团长予以阻止,事后仍久久不能释怀。
西北世态·民族情结
《日记》浓笔重彩地记载了特定时代背景下西北政局的要闻和社会风情,这些鲜活的史料,对于新疆近现代历史的研究是难得的详实文献。
在包头,刘衍淮将北大《风俗调查表》发放给当地学生;到达新疆,在博格达山采集哈萨克、回、塔塔尔族情歌;在库车,抄录、翻译维吾尔族曲子。《刘衍淮蒙新民歌抄本》30多首曲子,用拉丁字母记音、用该民族语言词汇解释,有全部曲子的汉译。独自一人搜集整理多个民族、多种语言的音乐素材,在同时期十分罕见,十分难得。
《日记》原汁原味地记录了见闻中的蒙古族婚姻、汉族庙会、柯尔克孜族在天山深处的放牧,以及南疆维吾尔族的巴扎、节日、跳皮尔治病、盖新房等习俗。
刘衍淮对考察途中所见种种落后现象,充满了批判精神。在库车,得知年逾花甲、三妻四妾的阿吉要娶维吾尔族十四五岁的幼女,为之愤愤不平,并对“官府视若无睹”深感痛心。《日记》多次提及鸦片种植,政府却大开绿灯,从而对刚刚北伐成功的国民政府表示了深深的失望。
求学德国·他乡月明
1929年11月科考结束,在斯文·赫定和郝德的帮助下,刘衍淮与李宪之决定赴德留学。次年,进入德国柏林大学(今柏林洪堡大学)攻读气象、地理与海洋学科。1934年,刘衍淮以德文论文《中国东南沿海气候与天气之研究》获得博士学位,成为继竺可桢之后,第二位获得这一学位的中国人。
刘衍淮参加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经历、他的讲演,广受师生们称赞,同时获得了一位少女——列美·巴丁娜的芳心。巴丁娜出生于西班牙巴塞罗那,父亲是著名教育家。巴丁娜获得马德里大学博士学位后,以优异的成绩得到奖学金资助前往柏林大学进修,得以邂逅刘衍淮。当时的德国正被狂热的种族主义所支配,官方不允许为一位中国人证婚,于是两人在中国驻柏林大使馆举行了婚礼。
1934年8月,刘衍淮学成归来,受聘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暨研究院研究员,兼任清华大学地学系讲师、气象台台长。
1935年,巴丁娜怀抱长子刘元来到久闻其名而又神秘陌生的国度——中国。次年春假,刘衍淮率家人回山东省平阴县探亲,因了文化的冲突、时代的局限以及世俗的偏见,这是一次并不愉快的行程,为两人的跨国姻缘系上了无形而沉重的镣铐。
1936年秋,经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竺可桢推荐,刘衍淮赴杭州出任中央航校气象教官兼气象台长,为抗战期间中国空军以少胜多、获得最后胜利,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后中央航校迁往大后方,刘衍淮一家先后迁居杭州笕桥、云南昆明,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路途。在南京至汉口的渡轮上,一家人幸运地躲过了日军轰炸,但巴丁娜所带行李大都随着另一艘驳船的沉没荡然无存。到达云南,住进昆明城郊的一个小村庄,刘衍淮着手创办、主持空军测候训练班,并负责气象台的管理。巴丁娜用奎宁治愈村民的疟疾,为他们缝制蚊帐阻隔传染病的蔓延。1945年日寇投降,刘衍淮一家转移到成都附近的凤凰山。临行之际,村民们献上了水果、干粮、火腿,依依不舍地挥别这位金发碧眼的邻居。
1949年12月,刘衍淮一家随军离开中国大陆,来到台湾南部的冈山,刘衍淮服役于冈山空军气象训练班。1960年7月,受聘担任台湾师范大学史地系主任兼教授,后创立地理研究所,任主任兼教授。1978年退休后兼任教授,担任中国台湾地区“中国地理学会”理事长。1982年10月5日,病逝于台北荣民总医院。
1960年巴丁娜走出家庭,在淡江学院、基隆海洋学院等处教授西班牙语和法语。她教学认真,爱学生如子女,替穷困学生缴纳学费。由于语言才华出众,教书生涯一直坚持到退休。后随子女移居美国。巴丁娜喜欢别人叫她“刘太太”,“我是个中国人”,她常常说。巴丁娜75岁时,将其人生经历写成《他乡月明》一书。1999年离世。
刘衍淮是我国气象事业的开拓者、气象教育的奠基人,开设过气象学、气候学、地理学、地形学、海洋学、数理地理、地图学、区域地理、地球科学、地球物理等课程。自1931年发表《天山南路的雨水》,直到晚年,写作了大量关于西北科学考察和考察团学术史的文章,包括去世当年发表的《斯文·赫定最后一次在我国西北的考察1933—1935》《中国与瑞典合组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(1927—1933)》,体现了他对气象事业开端时期的怀念。刘衍淮晚年回顾起这段科学考察,将之视为自己事业的起点,而他的《日记》则成为对这段特殊人生经历的真实写照。
2017年,在北京大学主办的《纪念中国西北科学考察九十周年展览》上,刘衍淮之女刘美丽代表刘家七个子女,将父亲刘衍淮的全部遗物捐赠给了中国学术机构。
刘衍淮的清华大学同窗、与其共同参与西北气象考察的李宪之(1904—2001),论著有《塔克拉玛干沙漠对若羌天气的影响》《东亚寒潮侵袭的研究》《台风的研究》,皆为研究寒潮和台风的奠基性、经典性著作,在国际气象界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。李宪之长期从事气象高等教育,在清华大学、西南联合大学、北京大学任教,培养出了大批气象事业的优秀人才,是我国气象科学研究和气象高等教育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,与刘衍淮并驾齐驱,同为海峡两岸气象学界泰斗级人物,最终应验了斯文·赫定“深信刘(刘衍淮)李(李宪之)二君对于世界科学将有重大贡献”的预判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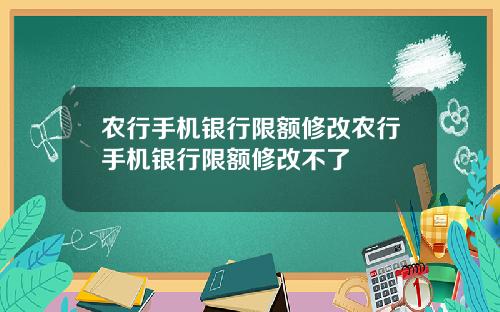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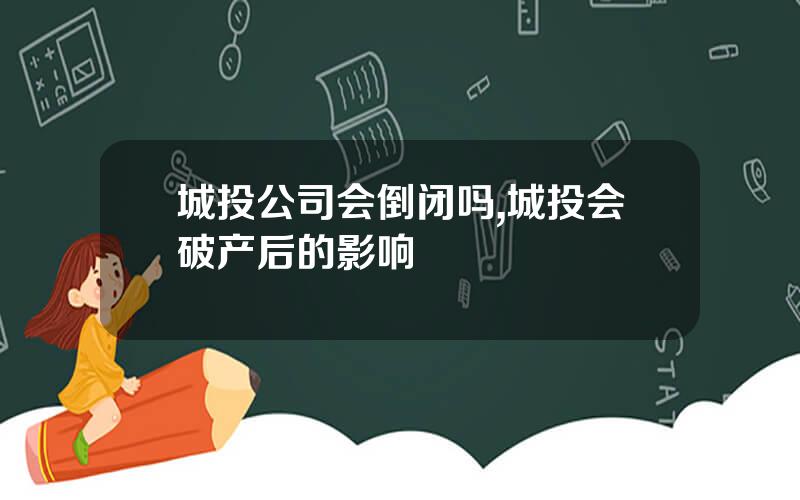

.jpg)